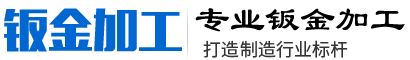HASH GAME - Online Skill Game GET 300

2024年春天,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抗议运动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席卷了美国内外的众多西方名校。2025年3月7日,特朗普政府以哥伦比亚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学生和教职员工”为由,宣布削减该校4亿美元的联邦经费。次日,此前抗议的主要组织人之一、巴勒斯坦籍美国绿卡持有者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遭到强行拘捕。3月13日,在发出威胁称其他60所大学也将经受同样命运之后,特朗普政府向哥伦比亚大学发出一封信件,要求其在3月20日之前表态遵守一系列来自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以作为恢复此前被削减经费的先决条件。在截止时间之前的几个小时,哥伦比亚大学发布了一份备忘录,默认了特朗普政府的大多数要求,其中包括禁止在校园内戴口罩,授权安保人员带走或逮捕个人,以及由校方接管教授中东相关课程的院系。
波洛克指出,Messas并未在组织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抗议活动中扮演任何角色,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针对Messas,显然是因为其教职人员没有在学术上坚定地支持以色列。美国政府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坚定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施暴的国家。与之相反,中东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的学术研究对局势的复杂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在很久以前就对助长以色列行为的历史版本和种族观念提出了质疑。Messas的教授们对以色列提出了尖锐但完全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美国政府试图禁止他们提问。美国政府直接干预院系管理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史无前例,此举将破坏美国大学的两个基本原则:院系自治和学术自由。在该文末尾,波洛克掷地有声地写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正常运作的司法系统,哥伦比亚大学对特朗普的回答就只能是:‘法庭上见’。”然而事情的发展显然并不如他所愿。
在波洛克的文章刊发的前一日,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杨-维尔纳·缪勒(Jan-Werner Müller)就在《卫报》发文号召大学挺身捍卫学术自由,并给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大学不应被公众舆论正在转向对立面的说法所吓倒,保守派并非天然反对大学,在其他民主国家,即使是投票给极右翼政党的选民一般也不反对大学;大学必须捍卫其求真和教育的使命,可以指出政府资助学术研究显而易见的益处,包括经济方面的好处,但必须坚持不能由政府来决定哪些院系是合法的哪些则应该被“接管”;大学必须避免陷入为保住硬科学而放弃人文学科的陷阱。他还呼吁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与学术界团结起来,守望相助。
与缪勒文中的积极乐观基调相比,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梅根·欧罗克(By Meghan OʼRourke)近日在《》发表的“为我们所知的大学的终结”(The End of the University as We Know It)一文似乎对美国大学的境遇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更符合实际的判断。文中指出,自20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开始热切资助高等教育以来,保守派一直试图重塑美国大学。但现在,特朗普政府似乎准备摧毁它。
欧罗克指出,这场向高等教育发动的攻击是与特朗普的保守派盟友酝酿已久的计划。其主要策划者克里斯托弗·鲁佛(Christopher Rufo)有着明确的策略:利用财政压力令大学陷入他所谓的“生存恐怖”,让服从成为看上去唯一可行的选项,迫使它们取消项目、重新调整招聘和课程设置。在特朗普在此当选后不久,鲁佛就受邀前往海湖庄园探讨高等教育改革问题,他认为大学被左翼意识形态所“俘虏”,并拒绝承认多元性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他想要对人文学科进行激进重组,用模糊的“古典”模式取代现有框架,同时引入更多的保守派教员。
她接着写道,这次猛攻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保守派长达数十年的攻击让公众将大学视为精英主义的灌输中心。这些攻击至少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红色恐慌”, 当时被怀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授被迫在参议院作证(联邦调查局将约400名教师和教授的不实信息泄露给了他们的雇主)。如今,这些攻击进化成了策略明确、资金充足的运动。研究高等教育和政治压迫的历史学家埃伦·施莱克(Ellen Schrecker)在202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战争期间......右翼慈善家们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将高等教育妖魔化为‘政治正确’泛滥的场所,并声称其倡导者们在散布教条主义的左翼身份政治的同时,压制校园内的和保守派叙事。在学费飙升导致私立院校越发高不可攀、大流行加深了人们对专业性的怀疑的背景下,特朗普及其盟友对上述信息的反复强调进一步加剧了共和党人对学术界的不信任。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2015年美国人中对高等教育很有信心和较有信心的比例为57%,2023年,这一数据下降至36%;在共和党人中,这一数据更是从56%暴跌至20%。这种不信任一部分来源于这样的事实:1990年代末,大学中自由派的教员人数增加,而温和派和保守派的人数下降。
尽管如此,欧罗克指出,承认美国的在执行校园规范和言论方面存在过激,和联邦政府动用国家权力阻止人们说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之间存在本质差别。正在展开的破坏不是对侵犯公民权利的指控的审慎反应,也不是对大学政策的微调改革。相反,它是一记重锤,砸碎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它会带来真正的、超越党派的破坏性后果。它将损害有利于美国及其世界地位的各类专业知识:癌症研究,妇产保健,与气候相关的技术……这对于经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其对于文化的影响亦然。真正发生的事情是,美国人对于知识作为一种价值和公益的信念正受到攻击,而这种信念在过去令他们获益良多。
文章接着回溯了美国历史上大学和联邦政府的关系演进。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 of 1862)建立了赠地大学制度,这是联邦政府为扩大高等教育所做的最初努力之一,使得大学与发展中的工业经济的需求相一致。1890年的《第二莫里尔法案》为过去的黑人学院和大学提供了资金,并强化了高等教育是公益事业的理念,它不仅服务于个人,也服务于国家更广泛的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则从根本上将大学转变为国家力量的引擎,将研究与军事和技术优势绑定在一起。大学在曼哈顿计划、雷达开发等项目中扮演了至关重要 的角色,从此,高等教育对于美国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变得不可或缺。到了1960年代,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掀起了全国性的科技教育热潮。联邦研发资金激增,不仅支持工程和军事项目,也支持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从1957年到196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大学提供的资助经费从4000万美元攀升至近5亿美元,大学成为政府支持的知识生产中心。
然而,这种安排也有其悖论。虽然大学依靠公共资金发展壮大,但其学生和教员中存在的左翼声音使其成为了保守派的靶子。里根在竞选加州州长时,就曾将伯克利大学的运动作为目标。1960年代末,尼克松政府讨论过因校园越战抗议削减大学经费的问题,尽管最终并未实行,但100多名非终身轨的教员因其政治行动而遭到解雇,各州也考虑过推出法案将参与校园抗议定罪。1991年,小布什总统抨击“政治正确”限制了“进取心、言论和精神力量”,并导致了“霸凌”。但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右翼似乎心照不宣地认为,尽管存在种种问题,现代研究型大学具备真正的价值,甚至是美国的一大竞争优势,是人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是软实力和国家品牌推广的工具。而当下这场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型大学作为自治机构的理念正在受到直接的攻击。
行文至此,欧罗克尝试回答一个棘手的问题:既然大学总是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政治化,那么保守派为什么要在意目前以自由派为主的院校中的学术自由呢?她的回答是,学术自由让我们有可能在被体制所统治时从内部批判体制,它允许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质疑我们感到自满的现实,为资本主义市场之外的价值观创造了空间,容纳了艺术和艺术家。尽管和所有社群一样,大学可能引起分歧、存在审查、有时在意识形态上过于单一,但当它发挥作用时,它训练人们批判性地、有力量地、坚定不移地思考。她举例称,对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最强烈的批评,并不是来自特朗普或马斯克,而是来自那些了解其运作并且拥有想象其变革的理论框架的人。
文章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命令下达于一个对于美国而言岌岌可危的时刻——一个科技变革、气候危机加剧和全球不稳定的时刻。人文学科的使命在此时尤为重要。为我们所知的人文学科是为了回应两次世界大战的暴力而出现的,因为这些冲突表明科学的进步并不能保证道德的进步。人文教育教会我们质疑主流叙事,发现某些思维方式是如何兴起的,其他思维方式又是如何淡出的。哈佛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前院长罗宾·凯尔西(Robin Kelsey)指出,“人文学科的核心矛盾之一是,它们一方面应该奉行和科学一样的怀疑主义、开放探究和拒绝教条原则,然而同时又要解决意义、美德和伦理等过去属于宗教范畴的问题”。这种矛盾使得人文学科既重要又脆弱,容易被认为其轻浮或政治上可疑的人攻击。
特朗普政府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撤资令美国学术界感到了寒意。显而易见的威胁是,各机构会为了保住资金而与政府最广泛的目标保持一致。而更深层次的威胁在于,如波兰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心灵》(The Captive Mind)中所写的那样,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艺术家和学者,即使没有受到直接的胁迫,也会预测政权的喜好,在政府干预之前就调整自己的行为。恐惧重塑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决定了他们会说什么和不说什么。一种与之相似的恐惧正在美国大学中弥漫开来。有人希望这个时刻将迫使大学重新思考其对开放探究的承诺,以知识和道德上的狭隘,但欧罗克对现状感到悲观。当受到攻击的是自由思想存在的条件,美国人可能还不知道其全部代价,但却会在未来数十年间感受到其后果。
因此,《破晓》更为直接的政治立场本就已经在桌游社区引发了一些争议。然而,真正引发轩然的,是该游戏的设计师梅纳帕斯在领奖时公开表达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在发表简短演讲“鼓励游戏设计师关注现实世界的挑战”后,梅纳帕斯自己的T恤上贴上了一枚贴纸,贴纸上印有巴勒斯坦的历史版图剪影,并带有西瓜的图案。(注:西瓜是巴勒斯坦抵抗的象征。自1967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以来,巴勒斯坦国旗在许多场合被禁止,但西瓜的红、黑、绿、白四色与巴勒斯坦国旗相同,因此成为象征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隐喻。)
她认为,电子游戏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具有政治动员和组织的潜力。然而,令人警惕的是,极右翼比进步力量更早意识到了游戏的政治价值。最著名的例子是 #Gamergate 事件。数千名玩家在极右翼影响者的号召下,针对游戏行业内的女性发起了恶意网络攻击,掀起了一场充满仇恨的在线运动。此外,《Roblox》这款受儿童和青少年喜爱的游戏,也成为极右翼组织的目标。美国NBC电视台的调查发现,该游戏内有 100 多个纳粹组织,试图在年轻玩家群体中招募成员。